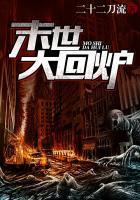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重启人生,我用金钱碾压一切 > 第一百零九章 黄昏起笔光落人心(第1页)
第一百零九章 黄昏起笔光落人心(第1页)
天刚亮时,小镇的屋顶还裹着一层薄雾。
秦川坐在旅馆的窗前,手里捧着一杯刚泡好的热茶,热气袅袅升起,和窗外那一抹淡白的晨雾交织在一起。
今天的空气格外清新,雨后未干的土壤味与不远处槐花的香味混合,静静渗入他的呼吸。
他换上了深蓝色的布衫,把昨夜晾干的帆布包背在肩上,准备去镇南边的老粮仓。
那是镇上准备改建成“社区故事馆”的旧建筑,几位年长居民提议用来陈列小镇往年的物件与照片。
他答应帮忙整理最早一批物料的登记与分类。
街道尚静,早餐摊上的火刚起,老板娘朝他摆摆手。
“小秦,今天早啊,等会儿油条再送你一根。”
他点头应了一声,走得不急。
沿着熟悉的石板路走到老粮仓,门口已聚了几人。
几位中年人正在清理门口的藤蔓,一位老人正在抬箱子。
他赶紧上前接过,搬进仓内。
里面的光线有些暗,老式木窗落着一层尘土,角落堆着几口老箱子和铁皮柜。
他先打开窗子,让光透进来,然后戴上手套开始清点。
箱子里有老照片,有破损的木尺,有三十年前的镇办粮票册,也有几张折痕密布的地图。
每一样东西拿在手里,都像拿起了一小段被时间压缩过的情绪。
有张照片特别引人注目。
是老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的人群,照片上的人神情各异,但都饱含期待。
一位老奶奶站在照片前笑着说。
“那年放《庐山恋》,我带我家老头子看了三次。”
她说话时语气平和,眼角却有了光。
秦川把这些照片一一分类,将破损的部分贴上保护膜,打上标签。
一位志愿者问他。
“你总是这么认真,是不是曾经干过这方面的工作?”
他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
“东西是旧的,但记忆要新着保。”
中午,他们围坐在仓外的大榆树下吃饭。
饭是各家带的,热菜装在铁饭盒里,凉菜铺在搪瓷盘上。
有人带了咸鸭蛋,有人带了炒韭菜,有人带了梅干菜烧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