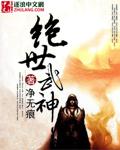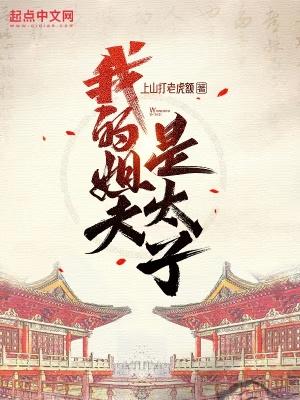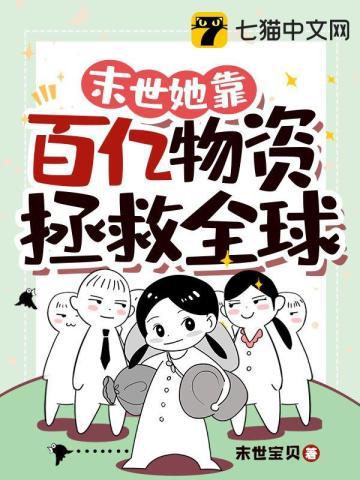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捡到花瓶将军后 > 弹劾(第1页)
弹劾(第1页)
那是一封弹劾章云烽的折子。
章云烽写了几年的战报和公文,对这种冗长华丽的骈体文章有了点研究,知道了怎么看这东西速度才能最快。
他直接略过了满是场面话的开头,一目十行地将折子中段扫了一遍。
折子中细细罗列了章云烽为将后的所作所为,言辞锐利地痛斥了章云烽的僭越之处,包括但不限于数次未能及时将战报派人送到京中,频繁改换军中军队布置,私自贬斥军中官员。
接着又对阳关口校尉叛变一事发表了长篇大论,一通分析,最后言之凿凿地得出结论——这都是章云烽治军不严的错。
章云烽看得只想发笑。
天地良心,他治军之严,已经到了连一向古板的祝迁,都看不下去的程度了。
这群人真是闭着眼睛胡思乱想,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章云烽把那些自作聪明的猜测只当放屁,目光在最末尾那句“此子狼子野心,恐有叛变之相”上顿了一下,而后恭恭敬敬地将折子往前一推,把脑袋往地上一磕:“臣不敢。”
“你不敢?”景帝的声音依旧平静,难辨喜怒,“你给朕说说,你不敢什么?”
章云烽垂首:“臣忠国忠君,不敢有二心。”
“哦,忠国忠君。”景帝慢悠悠点了点头,“为何不是忠君报国啊?”
殿内空气仿佛凝滞了一瞬。
章云烽心头微凛,他没想到景帝会抠这个字眼,景帝的目光轻飘飘地落在他身上,却压得人喘不过气。
夕阳渐落,晚霞斜照,殿内被染成一片赤红,章云烽的影子被拖得极长,正落在景帝脚边。
景帝静静地看着跪在殿下的章云烽,指尖轻轻敲击着龙椅扶手,发出细微却清晰的笃笃声。
秉笔太监极有眼色地将景帝案前烛台点起,火苗跃动,映得章云烽半边侧脸轮廓分明,下颌线绷得有些紧。
章云烽迅速压下那丝因被质问而起的波澜,在心中仔细斟酌了言辞,抬起头,目光坦然而真挚地迎上景帝的视线:“臣幼时在宫中,随诸皇子一同听您教导,您说的最多的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如今臣在边关,身为北疆守将,生死皆系于陛下江山安危,‘报国’二字,于臣来说,便是‘报君’,既‘忠君’二字早已融入骨血,此心此志,天地可鉴,又何须再在言语上分先后?”
章云烽说完,再次深深叩首,他的额头重重磕在金砖之上,发出一声沉闷声响。
他叩首后,并未立刻抬起,而是继续维持着这个绝对臣服的姿态,肩膀贴地,纹丝不动,如同磐石。
景帝没有说话,深沉目光落在殿下那颗紧贴着地面的头颅之上,仿佛要穿透那层恭顺的皮囊,看清其中的心思。
殿中落针可闻,金砖的寒意透过额头直抵颅骨,章云烽跪伏于地,能清晰地听到自己胸腔中略快的心跳。
“报国便是报君,此心此志,天地可鉴啊……”景帝慢条斯理地将章云烽方才话中的几句重复了一遍,语气缓慢,叫人辨不出其中喜怒。
“章云烽。”
景帝的目光扫过那本弹劾的折子,又落回章云烽身上:“抬起头来。”
章云烽依言抬头,脸上神色平静,目光坚定如炬,唯有额头因方才的叩首留下了一片清晰的红痕。
景帝的目光在那片红痕上停留了一瞬,随即移开,淡淡道:“你这份心……这份记性,很好,你幼时养在宫中,朕知道你是个好孩子,现在你到了北疆,朕也愿意相信你是个好臣子。”
章云烽乖顺垂首。
“不过——”景帝话锋一转,眯了眯眼,“阳关口校尉欲谋逆一事,你就真的毫无察觉?”
“臣确实早有预料,故而两年前,臣就调动北疆排布,在阳关安排了人手,探听他的动向。”章云烽一板一眼道,“此人心思深沉,且极为擅长煽风点火,为防止他策反臣安排的人手,臣还多次调整了军中布局,确保计划万无一失。”
景帝:“既然你两年前就察觉出这人不对劲,为何又要等他真的举兵谋逆,你才动手?”
“圣上明察,”章云烽先夸了景帝一句,而后一边看着他的脸色,一边解释,“此人在军中多年,也曾立有军功,他将谋反之心隐藏的极好,臣五年前才到北疆,资历尚浅,虽看出他心思不纯,但一直没有找到证据。”
“臣想着,臣不能因为一些捕风捉影的猜想,就给一位征战沙场多年,因伤才退居二线的老兵定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若是臣的猜想有误,那岂不是冤枉了功臣?”
“况且北疆战事频繁,臣守在檀口,不能常去阳关,加之他谋逆那几日,檀口城门正被牙北大军猛攻,臣忙于守城,未能及时发觉,这确实是臣之过失,望陛下降罪。”
章云烽说完这长长一段,又给景帝磕了个头,再次抬首时,他见景帝面色好了一些,心里略微地松了口气。
“原来是这样么。”
景帝唇角微抬,手指抚过桌上玉石镇纸,忽然冷笑了一声:“好一通话里有话、含沙射影之言,你倒是巧舌如簧。”
他将镇纸拿起,在桌上磕了磕:“你说你不愿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枉旁人,但朕怎么记得就在一个月前,你才用一个类似的罪名,惩处了军中一个裨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