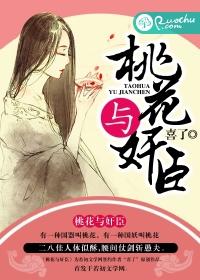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大明:哥,和尚没前途,咱造反吧 > 第一千一百五十三章 赌上一局天听(第2页)
第一千一百五十三章 赌上一局天听(第2页)
他步出讲堂之际,忽觉一人自廊下走来。
那人身形高大,步履稳重,一袭青绣蟒袍,正是朱瀚。
朱瀚似笑非笑:“你这一招,可算将齐王逼上了墙角。”
朱标沉默少许,才低声道:“是他先动的。”
“你既接下,那便做好落子。”
朱瀚拍了拍他肩膀,语气低沉,“你要的是未来,而非眼前胜负。”
朱标点头:“我明白。”
朱瀚忽然凑近,语气转轻:“不过有件事,该由我来。”
朱标一愣:“皇叔是说??”
“齐王。”朱瀚直视前方,眸中冷芒闪动。
“我要让他知道,藏在东宫背后的,不止是太子朱标,还有王爷朱瀚。”
三日后,京中忽传异闻。
永定门外,开坛讲道,群贤云集。
短短一日,便引得数百人围观听讲。
更惊人者,是朱瀚竞亲临其讲所之中,站在树荫之下,听完一整场演讲。
当讲毕之际,他甚至拍手而赞:“讲者心明志正,声可传国。
此语一出,满京皆惊。
暮色沉沉,长街人影渐散,唯永定门外那处“朝策讲所”依旧灯火通明。
讲坛之上,少年陈希文正据案而论,声如洪钟,引得堂下听者如云。
朱瀚立于榕树之下,手执象牙骨折扇,神情静谧如潭水。
风自西来,卷起他衣袍下摆,亦卷起了世人心思。
“他真的听完了?”齐王府中,李?低声问。
“从头听到尾,一句不落。”幕僚答得干脆,“还亲口夸了陈希文。”
李?面色阴沉,指尖紧握折扇,轻咯一声,扇骨微断。
“朱瀚何时这般喜欢多管闲事了?”
无人敢答。
当夜,王府书房中,沈镇将最后一页密报呈上。
“齐王疑虑已起,不过。。。。。。”他犹豫片刻,压低声音。
“属下更在意的,是那陈希文。今日讲道之中,他三次暗指“讲策之权当归太子,言辞虽有修饰,却显然非一般讲士所敢言。”
朱瀚淡淡应道:“他不是一般人。”
“哦?”
“他的父亲陈斐,原为前户部郎中,未入齐王党羽,三年前病卒,死前一言未留,却将所有书册数焚毁。”
沈镇挑眉:“清理门户?”
“或是留子避害。”朱瀚眼眸微凝,收拢折扇,“此子如今投东宫,未必全是为名。他心中定有更远打算。”
“那。。。。。。需不需除之?”
朱瀚摇头:“不急。”
他缓步走至窗前,望着远方灯火点点的永定门方向,低声道:“若他心有所图,便让他入局。’
“但局是我们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