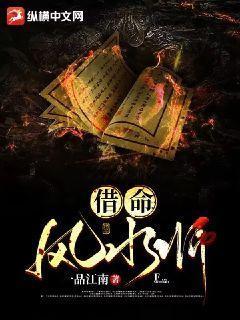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千娇面 > 揣度(第2页)
揣度(第2页)
长祚四十六年事暂且揭过,四十五年之事还未完。
若论长祚四十五年,有哪一日令水断栩刻骨铭心,应是得见叹秋尸首之日。
自“施入年案”后,除有劫后余生之感,便是对叹秋背叛的怨怼,她为此切齿拊心,恨海难填。
五年,五年相随左右,竟敌不过他人以利相诱,如此轻易背弃旧主,水断栩不禁疑惑,平日之叹秋,与那日书斋之叹秋,是否为同一人。
亦或是,最初,叹秋就是别有用心,蛰伏在她身旁五年,继而择一日显出本意来。
究竟是因何,水断栩不得而知,亦死无对证。
她只知晓,名为信任之赠礼,自己断不敢再交予他人,此举虽是以偏概全,可于她自己,却是万全之策。
经此一事,于水断栩是创巨痛深,创痍未瘳。
虽是此恨绵绵,她却在见到叹秋尸首之时,仍是不免惊诧。
叹秋死相极其惨烈,屠肠决眼,糜躯碎首,何人所见,皆会骇然噤息、悚气吞声。
“大人,这……要怎么处置?”
白布掀开,露出真容的刹那,玉盘当即惊呼,随即将自己双眼捂得严严实实,不漏一丝缝隙,战战兢兢地问询着。
“抛去义冢,若有人为其收尸,告知于我。”
话落,她眼前一切猝然远去,玉盘、叹秋的尸身、所有所有……
水断栩抬手欲捉住,可周遭皆从其指缝中流走,她无能为力,只能见景色徐徐变着,终至化为一荒废宅邸。
“娘子,娘子?您如何了?可是身子觉着不适?”
“娘子,您可别吓我们啊!柳姑娘,您快来瞧瞧!”
谙响一道道传至耳畔,水断栩经一回回唤着,渐渐目明。
入望便是玉盘同游乡二人焦灼的面容,二人口中絮絮叨叨,而柳诗痕在药囊中翻找着,自己则是被安置在椅上。
“我无碍,方才只是……只是一时怔然。”
“娘子您无事便好!不过……眼下如何收拾残局?”
水断栩闻言,起身环视周遭,血腥味仍旧挥之不去,莫论厅堂中残存血迹了,而几人衣裳,亦多多少少沾上了些,游乡所配的匕首上皆是殷红。
“对不住娘子,对不住玉盘姑娘,我……我此回太过冲动行事了。”
游乡垂下首,竭力将自己藏匿,来缓些愧疚。
“此时多说无益,还是想法子应对吧。”
此事棘手起来,牙婆又该如何安置?水断栩可未有如此多银子为其置办一处宅邸,银子可是要物尽其用,待牙婆身死,这宅邸留有何用?
牙婆还需将养身子,还需防她妄言妄语,无中生有。
水断栩竭力稳住心神,她知晓,若自己亦乱了方寸,她们会愈加焦灼。
“我此番进京,缘由有一便是回来投奔爹娘,自成了铃医,便许久未见他们,诸位大可前去寒舍。牙婆一事亦不用劳神费心,大可接去舍下,待何时有需,可来通传一声。此匕首……不知迎叶姑娘可愿赠予我?”
一侧的柳诗痕倏然开口,将每一事处置妥当,霎时间解了水断栩燃眉之急。
她大喜过望之余,不免惭愧,自己实属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注1】。
心中纵使还有隐隐忧心,亦不攻自破。
“这天色不早,还得尽快回府,事不宜迟!”
众人先是收拾了事发处,一行人继而走出荒废宅邸,正准行去柳家,水断栩与柳诗痕同行,玉盘则在末尾。
游乡搀扶着牙婆,行至中间,此一只手扶着腰,彼一只手握住其臂,徐徐前行着。
水断栩念起春月娘子亦住在东水巷,心中暗自祈求勿要遇上,一旦遇上,诸多疑问将问询出,自己亦难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