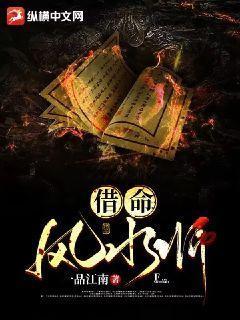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要宅斗不要武斗啊! > 我最好的朋友(第1页)
我最好的朋友(第1页)
“我也把眼睛蒙上啦。”
话音将落,于行宛摸索着走到门口,将门打开个缝,从中挤出去了。
奚燃被留在房中,一时怔住,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他缓缓浸入热汤中,水略有些烫,升腾起些白茫茫的雾气,早先被冷水冻得发麻的身体被包裹其中,被激得渐渐苏醒,一点点温暖起来。
奚燃呼出口气,随后又呼出口气来。
他的心,也像是被一团巨大的、暖融融的茫然包裹住了。
月光和烛火,将整个房间都照得亮堂堂的,触之所及都变得很柔软。
奚燃抬起只手,很轻地碰了下眼前覆带,不觉摸到些凸起来,是方才所未注意到的。
于是,他以指尖循着纹路,一点点向四周摸索,渐渐在脑中勾勒出完整的纹样。
于行宛在上面绣了朵花。
他摩挲着,弯起眼睛笑了。
。。。。。。
于行宛坐在隔壁房间的床上,不住地打呵欠。
奚燃的身体素质自然比她原先的身体好很多,可是,她仍不大习惯这样的长途跋涉。
这一日来,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她遭受这样一连串的冲击,身体和精神上都已精疲力尽。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于行宛困得快要倒下去睡着时,才听见墙壁传来咚咚咚三下声响。
她一个激灵,赶忙拍拍脸蛋,小跑着开门冲去隔壁房间。
要进去时,犹豫了一下,又拿出覆带蒙住了眼。
奚燃此时眼睛也蒙着,听见动静,循声望去,冲于行宛露出个笑。
于行宛有了先前撞到桌子的经历,这下走路便慢吞吞地,她一小步一小步往前挪,好大会儿走了一半路。
奚燃等得不耐,半埋怨半催促地说:“你出去一趟,回来便变成蜗牛了吗?从门口出发半天了也还没蹭过来,这样下去,马上就要天亮了。”
他说话夸张得很,于行宛敢怒不敢言,扁着嘴不说话,又听他讲,“你将覆带摘了罢,快点过来。”
她一时愣住了,有点犹豫地说:“不好罢?”
虽说是自己的身体,她倒是不介意,可是奚燃应当会不自在。
而且,她可不想呆会儿遵循旧制,等奚燃给她穿衣服的时候,也教奚燃睁着眼瞧她蒙眼光身子。
奚燃催她,“别墨迹。”
于行宛只好慢吞吞将覆带摘下,榻上人霎时映入眼帘。
难怪奚燃竟肯教她摘了覆带。
只见,他不知从哪儿找了块巨大的干巾,将整个人都裹住了,只露出张白净莹润的脸来,乌发湿漉漉地贴在身上,从脖颈处露出些许。
黑的发、瓷白的脖颈、被热气蒸出些红晕的脸,交织在毛毛的烛光中,恍惚间艳光大胜。于行宛一时竟认不出了。
她愣了下,心里怪怪的,又被催促两声,才快步行至榻前。
奚燃面朝向她,抬起下巴来,又将巾布向下拉,将一颗圆溜溜的头露出来,指挥她:“给我擦头发。”
于行宛乖乖应了,找来几条小些的干巾,按在湿发上吸水。
于行宛的头发很长,完全披散时及至腰际,要擦干好费一番功夫。
但于行宛很有耐心,她一寸寸地擦、一缕缕地擦,动作轻缓,生怕弄疼了他。
奚燃盘腿坐于榻上,眯着眼,嘴角翘起,一派怡然自得。
他摸到自己做的那条丑带子,被于行宛随手放在榻上,便扯到手里,指尖来回绕着玩,一边不忘跟于行宛讲话。
他絮絮说了许多小事,她都轻声应着。
奚燃整个人都被大的巾子、小的巾子围住,头发一点点退去湿意,浑身干燥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