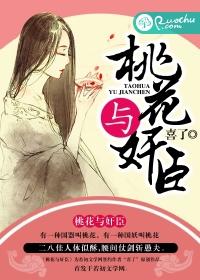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黑泥万人迷短篇合集 > 我的人渣男友二(第2页)
我的人渣男友二(第2页)
忙音嘟嘟地响起。
谢忱将听筒重重扣回话机,把烟蒂狠狠摁灭在电话亭脏污的内壁上,留下一个焦黑的印记。
他推开沉重的电话亭门,带着一身未散的烟味重新踏入逐渐喧嚣起来的街市。
他漫无目的地晃荡,走到一个书报摊前。
花花绿绿的杂志封面堆迭着。
他随手捡起一本。摊主是个干瘦老头,眼皮都不抬,没好气地嘟囔:“不买不要看,不要打扰我做生意!”
谢忱没说话,只是抬起头,那双浅色的眸子直勾勾地盯过去,没有温度。
老头被这目光刺得一激灵,抬头对上,剩下的半截话硬生生卡在喉咙里,脸色变了变,讪讪地摆摆手:“…算啦算啦,你睇啦。”声音明显弱了下去。
谢忱面无表情地翻了几页,彩页上光鲜亮丽的明星和富豪八卦,像是另一个世界,与他身处的这条弥漫着鱼腥味和汗臭的旧街格格不入。
他嗤笑一声,随手将杂志扔回摊上,转身离开。
日头渐渐毒辣起来,街道像被投入沸水的锅,人潮开始涌动。
谢忱不再走动,只是靠在一家关了门的卷闸门旁,身体微微后倾,目光淡漠地扫视着面前川流不息的人群。
穿着校服的学生仔嬉笑着跑过,提着菜篮的主妇行色匆匆,西装革履的白领夹着公文包一脸麻木…。。。与他无关。
快到中午,暑气蒸腾得地面发烫。
谢忱掐灭不知第几根烟,拐进一条窄巷里的糖水铺子。
铺子狭小,只摆着几张油腻的折迭桌,头顶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
阿祥背对着门口,正埋头对付一碗黑漆漆的芝麻糊,吃得满嘴乌黑,T恤后心洇开一片深色的汗渍。
谢忱拉开他对面那张塑料凳坐下,凳子腿摩擦水泥地,发出刺耳的噪音。
“今天去哪家?”
阿祥抬起头,嘴边糊了一圈黑。
他拿起桌上粗糙的纸巾胡乱抹了把嘴,把黑渍擦得满脸都是:“筒子楼,七楼左手边。扑街,上次阿生带几个兄弟去,刚拍门,里面那个老虔婆直接一桶粪水兜头淋落来!搞到阿生几日都洗唔甩阵味!”
谢忱没说话,只是站起身。
阿祥赶紧扒拉完最后两口,也跟了出去。
-----------
筒子楼矗立在密集的楼宇之间,外墙斑驳,爬满了暗绿色的苔藓和锈蚀的水痕。
楼道里光线昏暗,充斥着劣质烟草、腐烂垃圾和劣质杀虫剂混杂的呛人气味。
楼梯扶手锈蚀得厉害,脚下陈旧的木质楼梯随着每一步落下都发出痛苦的呻吟,似乎随时会断裂。
阿祥还在喋喋不休地咒骂着上次的遭遇。
谢忱面无表情,只是从裤袋里摸出烟盒,叼上一支点燃,猩红的火点在昏暗中明灭,映着他线条完美的侧脸。
七楼左手边那扇暗绿色的铁皮门,油漆剥落得厉害。
谢忱在门前站定,吸完最后一口烟,将烟蒂随手弹在积满灰尘的墙角。
他后退了小半步,猛地抬腿,军靴的厚底带着一股狠劲,狠狠踹在门锁附近。
“哐——!!!”
一声爆响,那扇本就单薄腐朽的门应声而开,门框处木屑飞溅,扭曲的锁舌直接崩飞出去。
谢忱在门开的瞬间就闪身而入,动作快得带风。阿祥紧跟其后。
逼仄的客厅里,一个满头灰白乱发的老太太和一个抱着小男孩的年轻女人正惊恐地望过来,脸色煞白。
阿祥脸上挤出一点虚假的笑意,目光却像刀子一样刮过那对祖孙:“老人家,上回你请我们兄弟饮嘅‘靓汤’,滋味难忘啊!今次我哋唔同你计较,你还钱就得嘞。”
老太太猛地啐了一口唾沫,浑浊的老眼里射出刻骨的恨意,枯瘦的手指颤抖着指向他们:“食人肉、饮人血嘅高利贷!我哋冇钱!钱系李永超借嘅!佢死咗!关我哋咩事!要还,你哋落去揾佢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