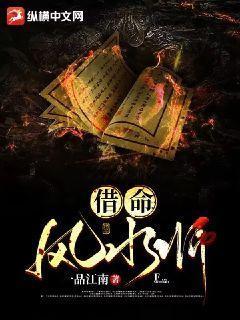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露水鸢尾 > Chapter 39(第4页)
Chapter 39(第4页)
“哦,再上次借过他的R8,我请他吃了顿饭,得知我大舅和他爸最近又因为什么纽约医疗基金受托,这样那样的,又合作上了嘛。”
安珏蓦然想到过年那会儿,倪稚京往小东巷搬了特别重的水果,远超她的能力范围。
想来那个时候,倪稚京和池叙就有苗头了?
可仅凭这些,就断言倪稚京在和池叙交往,好像有点武断了。
但安珏没再问下去。
毕竟对池叙,她实在无法大方表达祝福和赞成。
多诡异,她和倪稚京关系多么好,却不约而同地排斥彼此的对象。
倪稚京又喝完一杯:“问完我的事,我是不是也能问你了?现在你和袭野是什么情况?”
安珏愣了下:“他很忙,我们很少见面。嗯……今天早晨,他来家里见了奶奶。”
“我靠,这么快。是要提亲?”
“没有。就见个面,他拎了点礼物。和池叙今晚给你的这些差不多。”
至于分别时的那些不愉快,安珏不想提及。
停顿片晌,倪稚京又问:“盛长廉知道你们的事了?他同意?”
安珏反应了下,失笑。
她似乎只听过倪稚京连名带姓地称呼袭野父亲。而他们这些当事人作茧自缚,才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看作不能宣之于口的youknowwho。
安珏压着胸前的长发,低头喝了口粥:“他父亲不会同意的。”
“那他就这样耗着你?”
“你情我愿的事,合就聚,不合就散,没有谁耗着谁。”
倪稚京沉默须臾,叹气:“哎,要不怎么说年少时别遇到太惊艳的人呢。初恋真可怕,你也算是一见杨过误终身了。”
安珏笑了下:“大概吧。姜阿姨说得不对,以貌取人的不是你,是我。”
倪稚京撇嘴:“话也不能这么说,以貌取人咋了,生理性喜欢才是男女走到最后的关键。你想两个人吵得再凶,一看对方还是赏心悦目,走着走着,衣服脱了去床上吵——刚吵到哪?哦对,都讲了托洛斯基才是对的,苏联不可能独自完成快速工业化,修正主义害死人……死鬼,轻点啦……英特纳雄耐尔必将实现!”
安珏惊呆了:“我天,你小点声?”
倪稚京来的时候很平静,完全看不出醉意。
但吃酒切忌度数先高后低,特别容易醉。在倪家喝的是四五十度的白酒,而夜宵的扎啤不会超过五度。
这下可糟了。
安珏起身拉倪稚京,她却甩开,无缝切换下一话题:“对了,袭野就没问问你,怎么就沦落到了做调音师的境地?”
安珏摇头:“何至于沦落啊?我喜欢做这个事情。”
“因为你脑残,干一行爱一行。当年你多会念书啊,为什么高考没……我可是你的学习事业粉……狗男人他妈的问都不问?”
安珏无言以对。
她和袭野都对过去十年的事避而不谈,是心照不宣,不想揭开伤疤。
哪怕现阶段美好得有些不切实际,迟早要在现实的照妖镜下显出原形。
但物来则应物去不留,糊涂一时又何妨?
半晌,倪稚京嗷一嗓门又起来了:“对了,你和他复合就复合吧,千万做好避孕措施啊!”
食客们看过来了。
安珏人都麻了:“什么!我没有?”
“没有?难道他不行?不可能,他一看就贼有劲。那是你不行?你哪不行,要不要陪你去看病?”倪稚京重重地拍了桌子,“我以为你俩这样的,早就做到床板冒火星子了,结果跟我玩纯爱是吧?”
所有人都在笑。
安珏脑袋里简直在闪走马灯了,回过头,很少这样大声讲过话:“老板,结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