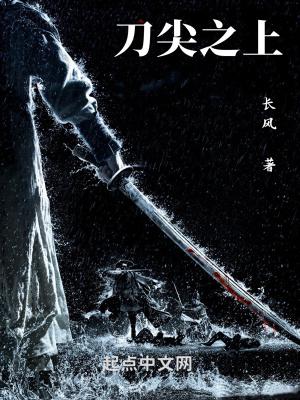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梦里南明客 > 鬼画符(第1页)
鬼画符(第1页)
“太子?”才打算离开的一群人又回了萍水庄,吴真来到狄玉仪身旁,驱散她关于那晚的记忆,“他来找你做什么。”
狄玉仪摇头,祥安来得突然,她猜不出狄珩启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以他惯常所为,此番想必不会有什么好事。”
祥安已在前院池边站定,他从怀中拿出个信封,并未第一时间交由狄玉仪。他环视四周抱臂紧盯自己的人,说道:“郡主,此事事关重大,最好不要有无关人士在场。”
狄玉仪看他一眼,浅淡开口:“殿下是否说过不可在人前查阅?”
“不曾,是卑职多嘴了。”祥安拱手赔礼,将信封递出,不再多言。
狄玉仪接过,自去坐下,将祥安晾在一旁。信件还没到手,便可瞧出厚度不薄,此刻捏在手里,两指隔出的间距倒好似拿了本书册。
封上未见名姓,封口上却像模像样打了火漆,似乎要证明祥安所言非虚。可在狄玉仪看来,这尽是狄珩启在故弄玄虚。她没兴致检查是否有旁人拆过,直接撕开外封。
信纸厚厚一叠,字迹是粗看似乎毫无章法的草书,而非狄珩启常写的端正楷字。狄玉仪随手一翻,每页都洋洋洒洒写满,不知道的,还当他们常似这般书信往来,回回都有说不尽的话。
狄玉仪耐着性子读完一张,尽是些虚情假意的思念感怀之语,她被狄珩启的废话连篇勾出心烦,这才叫起祥安,“殿下想说什么,还请直言。”
“抱歉,郡主。”祥安答得平板无趣,“卑职不知信中所写为何,殿下只嘱咐我送信。”
“那你又怎知事关重大?”狄玉仪不想惯着他们打哑谜,“若说不出,便还是请祥安将信件送回给殿下吧。平康的事,怎么也轮不到我来操心。”
“请郡主不要为难卑职。”
“自然可以。”狄玉仪很宽和,“告诉我这信里写了什么就好。”
祥安又是沉默,直等狄玉仪开口送客,他才学会讲话似的,“只知似与长公主有关,这才妄自揣测事关重大。还请郡主一览。”
狄玉仪笑说,“难怪你如此有恃无恐,原是等在这里。”
祥安并不反驳,没看出慌张,脸上明晃晃写着默认。
一听同长公主有关,旁边的叔伯姨母们,架势一下没端住,纷纷想看信里写的什么。他们拿起狄玉仪看完的那张,瞅了一会儿,个个骂天骂地,“写的什么玩意儿,会不会写字?”
“那便看看你们卖的什么关子。”狄玉仪令自己平心静气,只要显出丝毫急躁,待祥安回去一转述,狄珩启得到的乐趣越多。饶是如此劝过自己,翻开第二张信纸时,也险被他一句“袅袅吾妹”激得放下信纸。
真不知是来南明后,忍耐力有所下降,还是一段时间不见,狄珩启又将脸皮修厚一层。必是后者才对,狄玉仪暗自肯定,压下不适,这才重新往下看。
袅袅吾妹,日前耳闻一讯,深感震惊悲痛。一边为父皇、一边是吾妹,实不知如何抉择。然于情于理,吾妹该知真相。兄望一切皆为误会,兄盼吾妹勿要怨恨父皇。
这之后,狄珩启又写下大段的沉痛、悔恨、震惊之语,狄玉仪再翻两页,才算找出他耳闻的讯息是什么。
长公主非为自尽,她的死与和顺帝脱不了干系。
狄珩启看似写了千言万语,真正重要的东西却只轻飘飘地一句带过。他不提消息从何而来,证据在哪,也不提若真是如此,他怎敢就这样明目张胆送信至南明。
他只翻来覆去地,讲他父皇不会做下此等有悖人伦纲常之事;若真做下,也必是存有苦衷。狄珩启请她不要怨恨父皇,他愿代父受过。
“祥安当真不知信中内容?”狄玉仪将左手放在桌上,不让它颤抖。祥安再次摇头,她哂笑一声,将信纸往他身上一扔,“不知道?不知道你就敢替他送这等大逆不道的书信!”
狄玉仪骤然发怒,惊到院内众人。
她是真心愤怒,气母亲即便去世,也逃不过被狄珩启拿来消遣;但也是顺势为之,狄珩启见天想看她撕下温和面具,那就给他看,“你回去告诉狄珩启,我早已不需要装了。他爱演父慈子孝的戏码,便让他在平康演个够!”
祥安还没来得及答话,闻讯赶来的樊家人正到了院中。狄玉仪只觉眼前残影一闪,樊月瑶已一脚踹倒祥安,“哪里来的人,敢欺负玉仪姊姊!”
“啧。”樊循之紧随其后,将樊月瑶拉回来,“樊月瑶,这种时候不要抢我风头。”
樊循之看得分明,这男子第一反应便是回击,却硬生生压下了本能。他将樊月瑶推去娘亲身边,顺势拾起手边信纸,一看便皱眉,“什么鬼画符。”
“袅袅,这写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