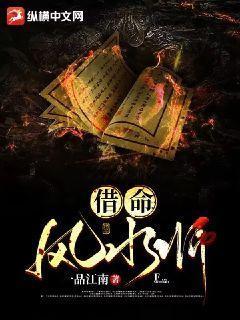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赘婿夫君他要登基 > 受伤(第2页)
受伤(第2页)
收拾好了汤碗,金婆子原是要退下去的,不知想到了什么,面露犹豫之色,在门口磨磨蹭蹭了好一会。
月祺然喝多了酒,心中也沉闷,不耐烦道:“有什么事就说。”
“哎,”金婆子半弯着腰,一句话在嘴里绕了几圈,才小心翼翼道:“小姐今日像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月少爷,在东院等了很久,饭都热了两遍,一直没等到月少爷回来,半夜才歇下。”
按理说这主子的事,做下人的,是不能多嘴的,只是明小姐为人和善,对下人也好,金婆子自是愿意为主子多操分心,这月少爷,身为明家的赘婿,对明小姐可是淡淡的,也不爱说话,金婆子想着,为小姐说说话,也省得小姐明日起来了都不开心。
只是金婆子等了好一会,都没见月祺然回话。她大着胆子,抬起眼皮朝月祺然望,只瞧见月祺然修长的手指捏着眉心,一双凤眼眯着,嘴唇抿成一条直线,满脸的烦躁与不耐。
正巧高毅提了热水进来,金婆子不敢再劝,赶忙小跑出去。
金老汉在门口提着灯笼等着金婆子一同回去,看着老妻额角冒汗,神色惶恐,压低了声音问道:“怎么了?你惹月少爷生气了?”
金婆子回头望了眼月祺然紧闭的门,拽着金老汉闷头往外走,小声回应:“我跟月少爷说小姐今夜等了许久,月少爷就生气了。”
“唉,不要多嘴。”金老汉叹气:“这当了赘婿的男人,哪有心中不怨妻家的,月少爷刚认了亲,还去书院读书,怕是心中更瞧不上赘婿这层身份,你这会子提小姐,不是火上浇油吗?!”
金婆子浑身一抖,悔不当初,忙拽着金老汉的手臂问:“那怎么办?我这不是害了小姐,万一月少爷觉得我仗势欺人,记恨小姐,明日她又要伤心了?”
金老汉摸了摸金婆子粗糙的手,慢悠悠道:“你啊,放心吧,你想啊,这月少爷虽然认了亲,可狄知州也没让月少爷搬出去,可见这婚约啊,还是板上钉钉。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等月少爷想通了,自然会哄着小姐的。”
而金老汉两口子走时,高毅站在月祺然房里,透过窗纸一直盯着金老汉和金婆子两人的灯笼消失在夜色里,又在西院周围巡视一圈,确定了此时西院没了其他人,才折返回去。
刚进门,高毅就半跪在月祺然身前,小心翼翼地撕开月祺然右腿外裤,雪蚕丝的里裤已被鲜血浸透,粘连在腿上,小腿肚上赫然一个小指宽的洞,半截箭头留在里面,创口处仍在汩汩流血。
“属下该死,护卫不利。您这伤口需要立刻处理,只是这···”
“无妨,直接处理吧。”月祺然动作没变,仍按着眉心哑声道:“粘连的衣物直接撕掉,把箭头拔出来,用七香凝血膏。”
高毅咬着牙,不再言语,将粘连在腿上和血肉混合在一起的里裤撕开,细碎的布头,用小刀一一刮掉,月祺然一声未吭,每一刀下去跳动的膝盖和强压下回原位的小腿,无一不展示着他所承受的痛苦。
只那么几下,高毅后背尽湿,大的创面清理干净,只剩拔出箭头。
他右手按住月祺然埋着箭头的创口两侧,突然问道:“公子,您和明小姐打算什么时候成婚?”
“成婚?呃···”月祺然闷哼一声,弹坐起身,满脸冷汗,他看着被甩在地上的一寸长的箭头,喘着粗气,半响直不起腰。
高毅说话间拔出箭头,头都没抬,赶忙将身侧的七香凝血膏涂抹在伤口上,此药疗效虽好,刺激性极大,费了好大的劲,才使得月祺然的右腿没有因刺痛挣脱。
待包扎好伤口,房间里的两人皆像水里捞出来似的,汗津津的。高毅长出口气,袖子在脸上胡乱一抹,擦去满脸的汗:“我扶公子上床歇下吧。”
月祺然咬紧牙关,惨白着脸点了点头,他的自尊与高傲,不允许他在属下面前痛呼出声。
直到高毅关闭了房门,他躲在柔软又舒适的云丝蚕被里,小声吸气。
今夜他与书院学子结交喝酒,趁着夜色夜访了酒楼隔壁的青楼,陆承与青娘暗地里查了许久,有一条暗线正巧断在了此地,却不想着普通的青楼里竟有功夫能媲美大内高手的人物,一时不查,他右腿被袖箭射中。
为掩人耳目,强忍了一晚上,才回来处理。
月祺然忍了许久,直至腿上的伤药镇痛的药劲渐渐上来,才放缓了急促的呼吸。
他躺在床上,目光转移到了书桌上的砚箱上,里面装着一只翡翠雕花玉簪,正是他母妃的遗物,也是她的,陪嫁之物。
月祺然无喜无悲的眼神盯着那箱子许久,他在心里告诉自己,这点伤算什么,跟他同样在吃苦的人更多,死了的人更多,这点伤不算什么。
浑然忘记了就在半年前,他连手指碰了一下,都会被丫环嬷嬷们围在一起,又是抹药又是安慰,好生一顿哄。
他想了一会,觉得口中发苦,连脊背都要直不起来,又想到明朝雨的几只玉钗,自然是没有宫中的水头好,连做工都不如,可是戴在那姑娘头上,盘绕的发髻中冒出一点点绿色,生动极了。
她今夜等了那么久,是想说些什么呢?
难道是看上了那送她水丞的书生,要跟他和离?
自然是不能。
月祺然转了身,阴沉的盯着面前的墙壁,他的人生已被一望无际的阴暗环绕,只剩这一抹翠色能点亮他的天空,他绝不会让这抹颜色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