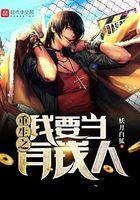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人在大明,无法无天 > 第769章 这里教的不仅是织布也是前程(第2页)
第769章 这里教的不仅是织布也是前程(第2页)
“当然。“春桃点亮油灯,“杭州工坊的规矩,工匠吃住都要最好的。“她指着墙上的章程,“每日做工四个时辰,十日休一天。受伤生病工坊包治,子女满六岁可以进义学。“
赵四媳妇突然哭了。她用袖子抹着眼泪:“我闺女要是在这儿该多好“
春桃拍拍她的肩膀:“等学成了,把家里人都接来。杭州工坊正在扩建,明年要招三百人呢。“
夜深了,寝舍渐渐安静下来。月光透过窗棂,照在墙上的《织工守则》上。最下面那行朱批格外醒目:“工匠是工坊的根本,待工匠如待家人。“
远处传来更夫的梆子声,杭州城的灯火像星河般闪烁。
第二天一早,杭州巾帼工坊的办公大院已经热闹非凡。春桃领着松江来的织工们穿过青石铺就的庭院,推开两扇朱漆大门时,二十多个女账房同时抬头的场面,让赵四媳妇手里的包袱啪嗒掉在了地上。
“这里是订单院。”春桃弯腰捡起包袱,拍了拍灰,“工坊所有买卖都要经这儿过手。”
三十张红木长案整齐排列,每张案前坐着一位女账房。她们左手按着账本,右手拨弄算盘,指尖翻飞间出清脆的声响。最前排的绿衣姑娘突然举起铜铃摇了摇,立刻有小厮捧着木盒跑来,盒里堆满盖着朱印的订单券。
“这是今早第三批南洋订单。”春桃指着西侧廊下几个番商,“他们专程从泉州赶来,就为订明年春天的提花布。”
赵四媳妇踮脚张望。一个戴珍珠耳环的番商正把银锭倒进大秤盘,穿蓝布褂的女账房拨动算珠,眨眼间就开出盖着骑缝章的订单券。那番商接过票据时,竟恭敬地行了个拱手礼。
“他们这么守规矩?”小桃姑娘拽春桃袖子。
春桃轻笑:“现在工坊的订单券比官银还硬气,南洋商队都抢着要。”
穿过前厅,中庭的景象更让人吃惊。八个月白衣裙的女子围坐在一张巨大的沙盘前,沙盘上插满各色小旗。见有人来,为的女子拿起长杆,指向沙盘中蜿蜒的运河模型。
“这是调度处。”春桃压低声音,“工坊所有货物运输都由她们安排。”
杆尖点在“松江”位置时,立刻有女子翻开册子念道:“明日辰时往松江的漕船,载新式织机五台、金线三箱、杭州匠人两名。”另一人迅在木牌上写下数字,挂到墙面的水运路线图上。
松江来的织工们看得入神。忽听一阵铜铃响,沙盘旁的小门里跑出个扎红头绳的姑娘,手里攥着刚盖印的文书:“急报!宁波港的番船提前到港,要加订两百匹金线布!”
“走陆路。”月白衣裙的女子毫不犹豫,“调二十匹快马,走官道送绍兴,再从绍兴换船。后日晌午前必须到港。”
春桃见众人疑惑,解释道:“番商最重信用,宁可赔本也要准时交货。上月暹罗商队因台风误期,工坊赔了双倍定金,反倒换来他们今年所有订单。”
转过回廊,后院的忙碌更甚。三十多个穿褐色短打的女子在条案间穿梭,案上堆满各色布样。有人核对订单,有人填写运单,还有人将木牌挂到墙面的巨幅地图上。每挂一块牌,就有小厮飞奔出去传令。
“这是核销处。”春桃指着东头案前的老妇人,“徐嬷嬷管了四十年漕运,闭着眼都能算出哪条水路最快。”
正说着,一个番商急匆匆闯进来,举着订单券大喊:“我的货呢?说好今日装船的!”
徐嬷嬷眼皮都不抬,枯瘦的手指往北面一指:“第三码头,乙字仓。巳时三刻的船,这会儿该过临平了。”
番商愣在原地。春桃抿嘴一笑:“工坊的货,说几时就几时。。”
日头渐高时,春桃带众人来到偏厅用饭。
八仙桌上摆着四菜一汤,竟比松江工坊的伙食还精细。
小桃姑娘刚端起碗,就听见窗外传来整齐的脚步声。
透过雕花窗棂,看见一队蓝衣娘子军扛着扁担列队走过,扁担上缠的红绸在风中猎猎作响。
“那是去码头押货的。”春桃给众人盛汤,“工坊规矩,贵重货物必须由娘子军押送。”
赵四媳妇突然放下筷子:“春桃姑娘,我……我能留下来学算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