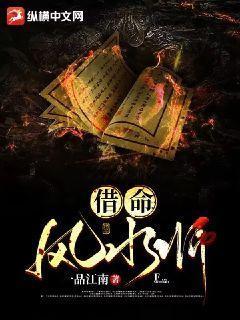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人在大明,无法无天 > 第728章 爷俩是一醉方休啊(第2页)
第728章 爷俩是一醉方休啊(第2页)
陈寒夹起片晶莹的皮冻,冻体里封着的桂花瓣在灯光下如同琥珀。
“那老顽固练废了三刀竹纸,最后在自家孙子的描红本上描了个歪扭的‘1’。”
冻块在舌尖化开的清凉中,他模仿着老臣颤抖的声调,“‘竖要直,圈要圆,这洋码子比馆阁体还磨人!’”
笑声震得梁上灰尘簌簌落下。
朱标忽然从袖中抖出卷皱巴巴的纸,展开竟是张染坊的进货单——阿拉伯数字旁密密麻麻标着朱批,最新一条写着“3日后交货”的“3”字被狠狠划掉,改写了个略显生硬的“3”。
“刘世叔家的账房昨夜闹出的笑话。”太子殿下蘸着酒水在桌面画了个圈,“那老先生把‘3。5’看成‘三又五’,硬说染坊进了三石五斗靛蓝。”
他指尖在圈里添了几道波纹,“气得刘家公子当场摔了砚台,嚷着要送他去巾帼工坊学算学。”
晚风送来糖醋鱼的酸甜气息。
陈寒舀了勺刚呈上的蟹粉豆腐,嫩白的豆花上缀着金黄油亮的蟹黄。“要说活学活用,还得看徐家。”
他吹散热气,“今早他们账房用‘1’和‘7’拼出个织机图样,说是要申请什么‘数字纹’的独家印鉴。”
朱标的银箸尖在豆腐上顿了顿,挑起的蟹黄丝拉得老长。
“那帮奸商!”他忽然失笑,“昨日还骂阿拉伯数字是蛮夷鬼画符,今日倒惦记起专利来了。”
豆腐在口中化开的鲜甜里,他忽然压低声音,“不过物理院那帮丫头更绝——听说她们用‘π’的符号设计出新织机的齿轮?”
酒过三巡,月光已爬上窗棂。
陈寒解开领口盘扣,拎起坛新开的绍兴黄晃了晃:“岳父可知道老郑头最近迷上什么?”
他斟酒时故意让酒液拉出细长的银线,“每晚让孙子教他背乘法口诀,背错一句就罚写十个‘8’字。”
“难怪他这几日奏章字迹飘!”朱标拍腿大笑,震得腰间玉佩叮当作响。
笑声未歇,忽听得窗外有窸窣动静几个小太监正扒着窗棂偷看,最年幼的那个手里还攥着本《算法统宗》。
陈寒推开雕花窗,夜风裹着桂花香扑面而来。
他变戏法似的摸出把铜钱撒出去,钱币落地时竟排成个规整的“9”字。
“去告诉御膳总管,再添道西湖醋鱼。”他转头对朱标眨眨眼,“要选三斤二两的草鱼——记得用新式秤!”
小太监们哄笑着散去后,朱标忽然正色:“说真的,你当初怎么想到用代金券废料染布?”
他指尖轻叩盏沿,“那日玄武湖畔,父皇盯着虹彩布的眼神,活像见了撒豆成兵的仙术。”
月光在酒面上碎成粼粼的银片。陈寒想起那锅沸腾的浆水,想起朱幼薇间沾着的纸浆碎屑。“是巾帼工坊的刘嬷嬷先现的。”
他夹了块新上的醋鱼,鱼肉在筷尖颤巍巍地抖,“她说废料煮出的水浆洗衣裳特别鲜亮,小桃那丫头便试着染了块帕子。”
鱼肉的酸甜在舌尖绽开,他仿佛又看见那日朱标蹲在染缸前,蟒袍下摆沾满七彩斑点的模样。“后来才明白,琉球海砂里的金属粉末与纸浆反应,就像……”
酒意上涌间,他随手用鱼骨在桌面排了个化学式,“就像新数字遇上旧账本,看着不相容,实则——”
“实则能炸出满堂彩!”朱标突然接话,银箸敲着瓷盘叮咚作响。
两人相视大笑,惊得窗外老槐树上的夜鹭扑棱棱飞起,羽翼掠过月亮时洒下一串清辉。
酒坛见底时,更夫的梆子声从远处传来。
朱标忽然醉醺醺地勾住陈寒肩膀:“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太子殿下指尖蘸着残酒,在桌上画了个歪扭的∞符号,“不是那些机巧明,是你能让守旧派自己打脸——老郑头现在逢人就夸阿拉伯数字防伪,刘世叔家的染坊账本全换成了新式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