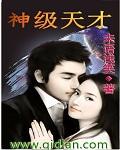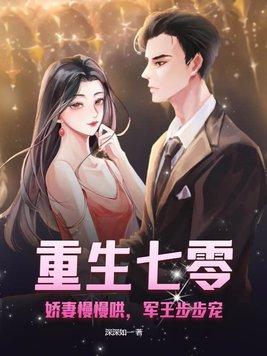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唯利是图 > 第291章 国营玉器厂(第3页)
第291章 国营玉器厂(第3页)
“就是这个多菌灵,本来乡上卖五块,我这一箱整批回来的,四块五就匀给大家!谁家棉田里看见叶子上有黄点子、烂斑疤的,赶紧买去打!打迟了耽误撇叉子,棉花秆子光蹿个儿不长桃,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四块五也确实比门市便宜。乡亲们纷纷围拢上来,有的掏票子,有的记账,三十包药眨眼功夫分了个精光。
苏阳抹了把额头上的汗,顾不上歇口气。
他又跑回自家地头。
于四海还在蹲在地里抽烟。
“四叔,给!”苏阳扔过去一包药,“把这个掺进去搅匀,喷水头反着打叶子,有用的很。”
苏阳也兑了进去,用力压气,出“哧咕、哧咕”的声音。
喷头里“嘶”地喷出扇面状的药雾,带着一股淡淡的硫磺苦味。
背上的喷雾器死沉死沉,压得肩膀像坠了两块青石板。
来回在棉田的垄沟里走,比挖玉累多了。
一个小时后,苏阳回到地头上,一连打了三桶药,两个肩膀火辣辣地胀痛。
回到家里,冷水管子底下冲了把脸。厨屋里苏老娘烙饼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可他顾不上吃,抓起件干净的汗衫套上,转身又骑上摩托朝城里去了。
今天的事可比吃饭要紧得多!
城里的风声他是费了老鼻子劲才打听到的,南关那家国营玉器厂,咬上了一大口肥肉:
刚从Qm县那边收进来一批顶好的黄口料!
他要趁着白菜价的时候,将这批料子给盘下来。只要价钱谈到位,那这批料子肯定就逃不脱。
如果可以的话,争取将整个市场上的黄口料全部垄断!
到时候黄口料的价格怎么定,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车子经过城南那灰扑扑、永远喧嚣混乱的火车站时,苏阳捏了下刹车,停在路边。
之前那些在出入口逗留的皮包客,现在都消失了。
经过上一次的严打,估计今年是不敢有人顶风作案了。
根据小胡警官的描述,窝点抄出来的那些‘造旧’的石料子,那做工,那皮色,那绺裂做得,连请去掌眼的几个老阿吉(对长者的尊称),凑在灯下都打瞪眼!要不是漏给他们了底,还真可能当籽料给收了!
苏阳拧了把油门,摩托车的吼声盖过了车站的喧哗。
南关,到了。
青砖围墙圈起来的国营大厂就杵在眼前。
厂子那两扇厚重的绿漆大铁门紧闭着,门口却已乌泱泱蹲守了十来个人。
每人脚边都蹬着个鼓囊囊的白色化肥袋子,手里攥着十字镐,眼神跟黏了胶似的,死死扒在门缝里透出的厂区动静上。
这些“碎石客”,做的就是厂子嘴里“不值钱”的营生。
只等厂里机器一停,那些切割雕刻剩下来的边角碎料、疙瘩块块,连同磨盘底下扫出来的玉粉末末,会被杂工一股脑儿用地板车推出来,倒进大门外不远处那个早已填了半满的碎石大土坑。
等厂子大门打开的时候,他们手脚麻利得像梳头,在杂乱的废石堆里翻、拣、抠、撬。
挑出来的东西也各有门道,稍微齐整点的碎块,拿回去磨个戒面、车个生肖小挂坠;小拇指肚大小的零碎,攒起来打珠子穿手串;实在不成器的粉屑末末,也有二道贩子收去——听说掺在玻璃或者塑料里做假货,或者给某些药铺当什么镇惊粉。
这库尔勒玉器厂,确实是南疆响当当的国营大厂。
附近几个县的公家矿坑出的籽料、山料片子,许多都要拉到这里切割打磨。
厂子架子大、路子硬,正经好料都干不完呢,自然瞧不上这点“石渣渣”。
现在他们袋子里都沉甸甸的,看样子都有收获。
苏阳刚走过去,十几双眼睛就扫了过来。
“呦呵,新面孔。”
还以为是又来了新人跟他们抢活。
自然是充满了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