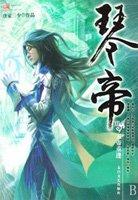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大明:哥,和尚没前途,咱造反吧 > 第一千一百四十二章 布子的机会(第2页)
第一千一百四十二章 布子的机会(第2页)
第二日清晨,沈仲文忽被罢官,京中哗然。
而朱标则在朝堂之上,步步紧逼,对朝政作出一系列调度,大胆启用年青新臣,悉数调任几个多年的“闲散太监”入东宫为辅,动作雷厉风行。
然而,这一番动作也惊动了朝中几位年深日久的老臣。
礼部尚书霍文济便于三日后公开上疏,言太子年幼急躁,动摇根本,不识大体。
朱标并未回应,只是在次日的早朝上,当众诏令:“礼部尚书霍文济,年高而无建,诛心而不辅政,着令罢职,令其归老。”
殿中一片哗然。朱元璋并未出言阻止。
朱瀚那日也站于班列之中,望着朱标的背影,心中微动。
“标儿,已真长大了。”
午后,他回府途中,车刚入巷口,便见一位身着青衫的文士匆匆拦道,正是王府旧识陈羽。
他一见朱瀚便行礼。
“王爷,京中已乱作一团,您当心些。今日有不明势力在坊市中散布言论,说太子专权,王爷您暗中撑腰,引人非议。”
朱瀚眯眼:“背后何人?”
陈羽低声:“疑是钱氏兄弟。”
朱瀚闻言冷笑:“原来如此。”
当夜,王府暗卫便出动。
三日后,钱氏兄弟俱被贬去岭南,口谕一封,盖有皇印,事情就此平息。
朱标得信后,悄然入王府拜见朱瀚。
“皇叔,您替我平了这场风波。”
朱瀚不语,举杯饮尽,方道:“记住,真正的皇者,从来不靠人说的风评活着,靠的是手中握得紧的利刃与人心。”
朱标郑重其事地鞠了一躬:“我会记得。”
北风卷雪,拍打着琉璃瓦檐,京师一夜未眠。
朱瀚披着玄狐大氅,立于王府正厅檐下,仰头望着天边渐泛鱼肚白的晨曦。
耳畔传来靴踏积雪之声,朱瀚转头,只见魏进从阴影中快步而来,躬身一礼。
“王爷,万寿寺中之事,已办妥。”
朱瀚点了点头:“按原计划,别惊动旁人。”
魏进略顿,道:“可那位静如师父,却主动见了我们,还说。。。。。。若是殿下亲至,她愿再言一番。”
朱瀚眉峰微挑,转身往屋内走去:“静如那婆子,倒是活得越来越明白了。
三刻钟后,王府轿撵悄然出发,低调驶向西山万寿寺。
此时的朱标,正坐于东宫书房内,一卷卷奏疏铺于案前,却无心批阅。
自那场“静退”之争后,朝局虽暂平,可宫中暗潮未息,父皇病情反复,便如一柄无鞘利剑,悬在每一位权臣心头。
“皇叔为何此时去见万寿寺静如?”朱标喃喃问道。
待立一旁的中允杨复之答道:“静如法号虽不在朝籍,但其旧年曾为崔阁老之女,家世不凡,且通文法,熟礼制,乃宫中几位嫔妃私下求教者。王爷或许是欲借她之言,探些动静。”
朱标眼神微变,旋即下令:“备马,我也去。”
而此时的万寿寺内,梵音袅袅,松风穿廊。